焦慮:對自我的威脅
我們經常聽到人們說,如果他們能夠回到母親的子宮裡就好了,因為那是最安全的世界,他們不必應對現實的各種可能性。作為胎兒,他們的需求得到毫不延遲的滿足。從那個安全的環境突然被拋入現實世界,那裡有如此多的東西需要同時感知,孩子變得對其周圍環境一無所知,並且難以應對——這種不友好的變化,即被置於如此敵對的環境中,會導致未來對創傷經歷的反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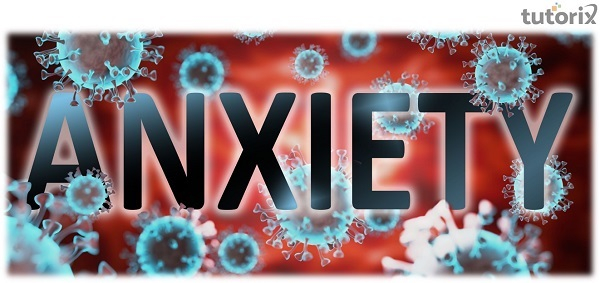
什麼是焦慮?
根據弗洛伊德的理論,出生創傷是我們第一次遇到焦慮,它是源於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間衝突的恐懼。無法應對這種焦慮並任其升級到我們面臨被壓垮的危險的程度,這意味著它已經變成了創傷。弗洛伊德的意思是,無論年齡或成熟度如何,我們肯定都會淪為一種猶豫不決的無助狀態,這會讓我們感到焦慮並威脅到自我的神聖性。弗洛伊德最初認為焦慮在很大程度上起源於性。無法表達的性思想和衝動被壓抑,然後轉化為某種象徵性的表現形式。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關於“焦慮”概念發展階段

最早的焦慮理論可以追溯到19世紀90年代中期,當時弗洛伊德將焦慮與性聯絡起來,將其定義為轉化為焦慮的性興奮。這是有毒階段,它認為當滿足途徑被阻斷時,未滿足的力比多能量透過獲取有毒特性而積聚,最終在焦慮中得到釋放。
由此,弗洛伊德將焦慮定義為源於壓抑的現象,壓抑發生在社會道德規範阻礙性衝動時。因此,他的“有毒理論”被修改為包括對性釋放的內部阻礙,而不是僅僅關注外部阻礙。
在最初將焦慮視為一種被修改的力比多之後,弗洛伊德在20世紀20年代後期開始發展一種新的、截然不同的焦慮理論。這是第三階段。在這裡,他做了一個重要的二分法:
自動焦慮:一種更主要的創傷性和現實導向的焦慮,其中“無助的自我”被壓垮。它是在此類創傷經歷中引發的感情反應,可以追溯到當孩子出生時,心理系統經歷大量新刺激的艱難過渡。
訊號焦慮:這可以理解為自我對危險情況的反應,在這種情況下,它是即將發生的危險或創傷情況的預警訊號,以便可以啟用防禦措施以防範它們。
這個最終階段賦予焦慮在心理運作中更加中心的地位:它不再是壓抑的一種副作用,現在可以將心靈本身的輪廓,包括其防禦和症狀,視為首先是為了避免焦慮。
焦慮的型別
弗洛伊德提出了三種不同型別的焦慮
- 現實焦慮
- 神經症焦慮
- 道德焦慮

現實焦慮:它也被稱為“客觀焦慮”,其他兩種型別都源於它。顧名思義,它源於現實——對現實世界中真實危險的恐懼,例如我們對火災、颶風、風暴、地震、野生動物和其他毀滅性世界威脅的合理恐懼。它旨在指導個人的行為,要麼保護自己,要麼逃離現實危險。當然,一旦威脅消失,恐懼也會消散。但是,如果恐懼使我們喪失能力並阻礙我們的日常生活,那麼這些基於現實的恐懼就被認為偏離了正常狀態,並走向極端。例如,一個人因為害怕地震導致建築物倒塌而不敢走樓梯,或者因為害怕被飛馳的汽車撞到而不敢過馬路。
神經症焦慮:神經症焦慮的基礎是在童年時期,當一個人經常陷入獲得即時滿足和麵對現實領域之間的衝突時。它被描述為自我體驗到的壓倒性感覺,因為本我威脅要在我們的思想和行為中展現其非理性,並且持續困擾著我們的內心。兒童經常因為公開表達性或攻擊性衝動而受到懲罰。因此,焦慮的產生源於滿足某些本我衝動的願望。神經症焦慮與一種無意識的恐懼有關,即害怕因表現出不討人喜歡的以本我為主導的行為而受到斥責,而很少或根本不考慮現實。但是,重要的是要理解,本能不會產生恐懼,而是滿足本能會導致的結果。
道德焦慮:道德焦慮是尋求快樂的本我和道德驅使的超我之間衝突的結果。它表達了超我的發展程度以及個人“受良心驅使”的程度。每當本我威脅要預示其與我們內在道德規範不一致的本能衝動之一時,超我就會透過在我們內心產生的羞愧或內疚感進行報復。與道德規範相對較低的人相比,具有強烈抑制良知的人肯定會經歷更大的衝突。它也以現實為基礎,即父母在兒童時期因違反其行為道德規範而給予的懲罰,或者成年人因違反社會道德規範而受到的懲罰。總而言之,這是一種感覺,即如果自我沒有根據超我的標準處理本我的衝動,那麼一個人的內化價值觀即將受到損害。
結論
焦慮向個人發出警告,表明人格內部存在某些問題。它在身體中引起一定程度的緊張,這驅使個人或激勵他們去滿足或減少它,就像滿足飢餓或口渴一樣。它充當一種警報,表明自我受到威脅,因此,除非採取行動,否則自我可能面臨被推翻的危險。因此,如果基本焦慮消失,將不會有保護自我的警示訊號。但是,如果它超過正常水平,自我再次面臨危險。因此,自我必須成為本我和超我之間的橋樑,並不斷努力實現和諧。


 資料結構
資料結構 網路
網路 關係型資料庫管理系統
關係型資料庫管理系統 作業系統
作業系統 Java
Java iOS
iOS HTML
HTML CSS
CSS Android
Android Python
Python C 語言程式設計
C 語言程式設計 C++
C++ C#
C# MongoDB
MongoDB MySQL
MySQL Javascript
Javascript PHP
PHP